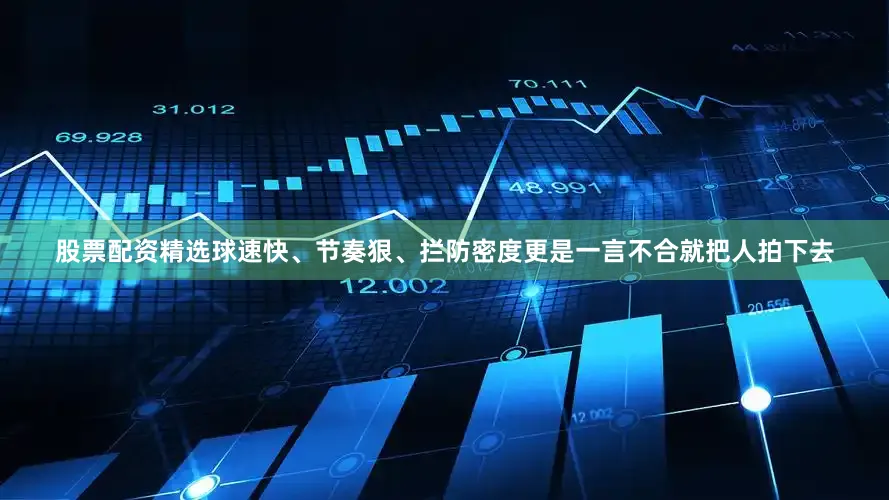气得发抖!乾隆重臣立的碑,200年安然无恙,咋在新公园里断了?
有些地方,你以为再去还和从前一样,结果现实能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十几年前,我头一回去商洛,山路绕得人晕头转向,就是为了亲眼瞅瞅那个传说中的四皓墓。
那时候,地方还没怎么开发,整个墓园子透着一股子荒凉又真实的历史劲儿。就在一堵破墙根底下,孤零零地立着一块石碑,上头“汉四皓墓”四个大字,是清朝乾隆爷那时候的陕西巡抚毕沅题的。那感觉,绝了,就像是跟几百年前的老古董打了个照面,特有味儿。
一晃十多年过去,前阵子我又溜达到商洛,听说那儿修了个气派的四皓公园,心想这回可得好好看看。
公园是真漂亮,绿树成荫,小桥流水,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可我走到墓前,一眼就看到了那块老石碑,当时我这心啊,就跟掉冰窖里一样,凉了半截。

好家伙,那石碑竟然从中间齐刷刷地断了,成了两半,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。中间还崩掉了一大块,像是被人硬生生啃了一口。原本青灰色的老皮子,现在也变得土黄土黄的,跟刚从泥里刨出来似的。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,脑袋里嗡嗡的,就一个念头:这十几年,它到底遭了什么罪?
这可不是一般的石头疙瘩,这是毕沅的碑。
说起毕沅这个人,那在清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他可不是个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官,人家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郎,学问做得顶天了。他当官,一路干到陕西巡抚,管着一省的军政大权。但他心里最放不下的,还是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遗迹。
他有个癖好,就是走到哪儿,看到哪个名人墓葬快被荒草埋了,就自掏腰包或者动员地方,给人家修缮一下,再亲笔题写一块碑立上。他写的字,是工工整整的隶书,沉稳大气。他搞这个事,不是为了显摆自己,是真打心眼儿里敬畏历史。他主持编修的《续资治通鉴》,到现在都是研究历史绕不开的大家伙。

毕沅这一辈子,在陕西各地立了少说也有几十块碑,给黄帝、给司马迁、给蔡伦……个个都是青史上留了名号的大人物。这些“毕沅碑”本身,就成了文物,是那段历史的见证。
可眼前这块,就这么废了。断口处,能看到有人用白色的胶状物给粘了粘,可那缺失的一大块,让“陕西巡抚”几个字都残缺不全,看着就跟一张被人撕碎了又胡乱拼凑起来的旧照片,别提多别扭了。
当年立碑的商州知事娄杰,要是泉下有知,看到自己当年费心费力竖起来的宝贝疙瘩成了这副模样,估计得气得从坟里爬出来。
再说这墓里躺着的“四皓”,那也不是一般人。这四位老先生,叫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,是秦末汉初天下闻名的四个大学问家。

当年刘邦得了天下,想请他们出山辅佐自己,四位老爷子压根不搭理他,说我们看不上你这个流氓皇帝,宁可在商山上采芝、钓鱼,过自己的清净日子。刘邦碰了一鼻子灰,也没办法。
后来,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,改立自己宠爱的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。吕后急了,到处找人想办法。谋士张良给她出了个主意,说你得想办法把商山四皓请出山,让他们天天陪着太子读书。这四位名满天下,连皇上都请不动,要是他们都认可太子,那太子的位子就稳了。
吕后也是下了血本,又是送礼又是派太子亲自去请,言辞恳切,姿态放得极低。四位老先生一看,觉得这太子刘盈仁厚恭谦,值得一帮,就答应出山了。
在一次宴会上,刘邦看到太子身后跟着四个白发苍苍、仙风道骨的老头,一打听,嘿,竟然是自己当年请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。他当时就明白了,太子羽翼已丰,动不了了。他对戚夫人说:“我想换掉他,可那四个人都来帮他了,翅膀硬了,唉,你以后就跟着他跳舞吧。”这事儿,直接保住了汉惠帝的江山。

这么四位连开国皇帝都得敬三分的人物,他们的安息之所,配得上毕沅这样的大官来给立碑。
可就是这么一块有故事、有来历、有分量的石碑,在安然度过了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,偏偏在环境优美、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公园里,落得个“身首异处”的下场。
这事儿,你说怪谁?是修公园的工人不小心碰倒了?还是哪个熊孩子手欠给推倒了?或者是在所谓的“保护”过程中,方法不对,好心办了坏事?那层土黄的颜色,让人不禁怀疑,它是不是在施工期间被埋进土里,后来又被粗暴地挖了出来。
想想毕沅给汉中那位造纸的蔡伦立的碑,至今还保存得相当完好,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文化符号。两块碑,同一个“爹”,命运却天差地别,真是让人五味杂陈。
我不是说修公园不好,把一个荒草丛生的地方变得整洁漂亮,让更多人能走近历史,这初衷绝对是好的。可问题是,我们在追求“新”和“美”的时候,是不是把最重要的那个“真”字给弄丢了?
那块断裂的石碑,就像一道刺眼的伤疤,刻在了崭新的公园脸上。它无声地诉说着一种尴尬:我们有钱有技术把环境修得美轮美奂,却没有能力,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敬畏心,去守护好一件脆弱的老物件。
有时候,最好的保护,或许就是不去打扰。让它在原来的地方,带着一身尘土和青苔,静静地站着,那份饱经沧桑的厚重感,比任何光鲜亮丽的修复都更有力量。
这事儿,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。
炒股配资官网开户,景逸策略,配资平台实盘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